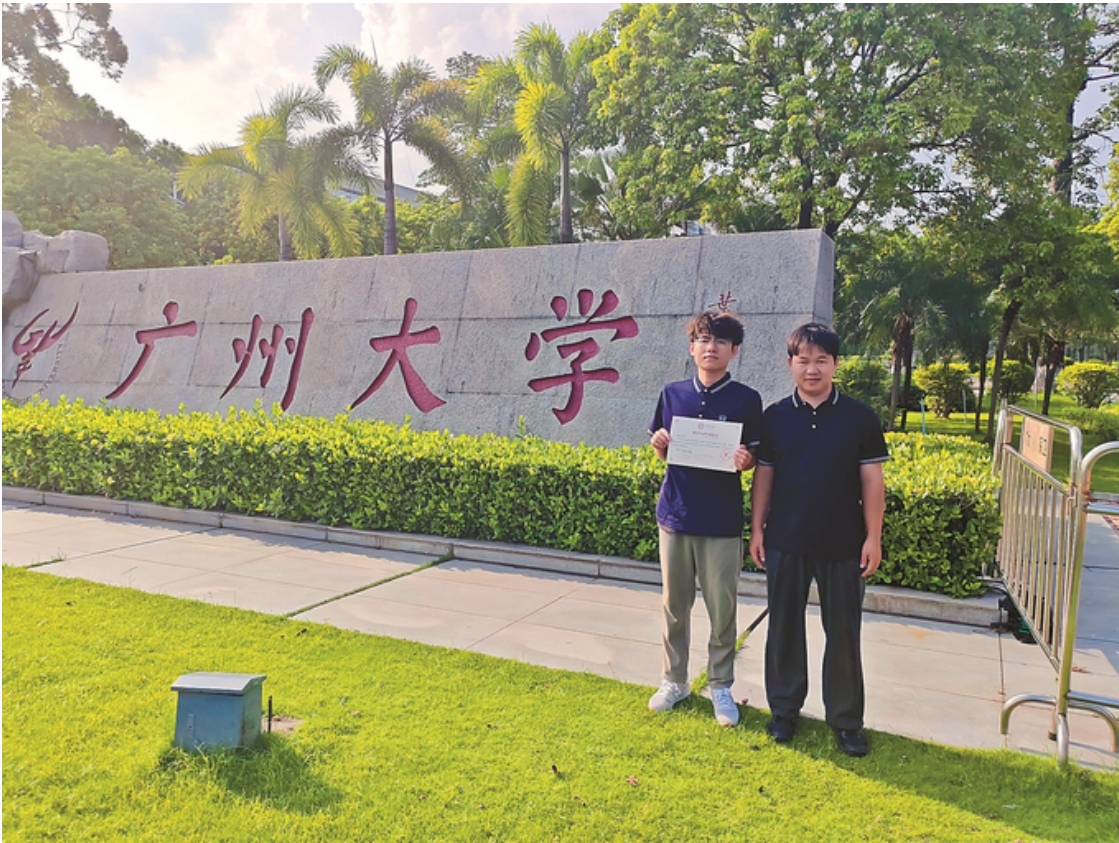
覃福雨(右)和師弟周標(biāo)勝的合照。(覃福雨供圖)
“看這邊,茄子!”7月的廣州驕陽(yáng)似火,覃福雨帶著剛考上博士的師弟周標(biāo)勝,在母校廣州大學(xué)門口留下了一張合影。“咔擦”一聲,定格的不只是青春的笑顏,更是一段關(guān)于夢(mèng)想與傳承的動(dòng)人故事。
“周哥,我終于成為和你們一樣的人了!”拍完照片,覃福雨忍不住打了個(gè)電話,聲音里帶著掩飾不住的喜悅。他口中的周哥,是廣西韋拔群干部學(xué)院黨委委員、副院長(zhǎng)周理。兩人的故事,還要從2017年說(shuō)起。
那年夏天,剛從武漢大學(xué)博士畢業(yè)的周理,放棄了大城市的發(fā)展機(jī)會(huì),選擇以定向選調(diào)生的身份來(lái)到廣西工作。在那里,他遇見了覃福雨,一個(gè)來(lái)自南寧市馬山縣的18歲少年。
“第一眼看到覃福雨,就被他眼里的疲憊感震撼到了,那不該是一個(gè)18歲少年該有的眼神。”周理回憶。深入交談后,周理才明白這份沉重從何而來(lái):剛剛收到的桂林電子科技大學(xué)錄取通知書,本該是他開啟人生新篇章的鑰匙,但7000元學(xué)費(fèi)成了壓在全家人心頭的巨石。覃福雨是離異家庭的孩子,全家僅靠母親打零工勉強(qiáng)糊口,是繼續(xù)求學(xué)還是提前打工?這個(gè)本該充滿希望的夏天,對(duì)覃福雨而言,卻充滿了迷茫與掙扎。
命運(yùn)的轉(zhuǎn)機(jī)出現(xiàn)在一個(gè)尋常的傍晚。周理帶著一個(gè)紅包,來(lái)到了覃福雨家中。“這是我們2017年廣西定向選調(diào)生的第一個(gè)月工資,一點(diǎn)心意,你先拿著,不夠再跟我說(shuō)。”周理將錢遞了過去。
“不,我不能要……”覃福雨像被燙到一般縮回了手。
“這是我們的心意。”周理的聲音溫和而堅(jiān)定,“以后你走出去了,再去幫助更多人,就是對(duì)我們最好的回報(bào)。” 那天,兩人坐在村口的石頭上聊了很久。晚霞染紅了天際,他們的影子被拉得很長(zhǎng),深深印在泥濘的村路上,也烙進(jìn)了覃福雨的心里。
夜深人靜時(shí),覃福雨在筆記本的扉頁(yè)鄭重寫下:“我要成為像周哥一樣的人!”這不僅僅是一句誓言,更是一顆深埋于土壤中的種子,靜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。
在周理的幫助下,覃福雨如愿踏進(jìn)大學(xué)校門。兩人亦師亦友的情誼,在無(wú)數(shù)個(gè)深夜的微信聊天中愈發(fā)深厚。“周哥,像我這樣的山里娃,真能靠讀書改變命運(yùn)嗎?”一個(gè)輾轉(zhuǎn)難眠的夜晚,覃福雨終于問出了這個(gè)壓在心底的問題。
“當(dāng)然能!”周理斬釘截鐵地說(shuō),“你不僅要讀完大學(xué),還要繼續(xù)讀研、讀博!”這期許化作少年書桌上越摞越高的筆記和深夜臺(tái)燈下倔強(qiáng)的剪影。
周理深知,改變一個(gè)人的命運(yùn)遠(yuǎn)遠(yuǎn)不夠,還要照亮整個(gè)村莊的希望。2021年,他主動(dòng)請(qǐng)纓來(lái)到馬山縣古寨瑤族鄉(xiāng)古棠村擔(dān)任駐村第一書記。那些年,他磨破3雙膠鞋,走遍每一戶人家;建起全縣首個(gè)鄉(xiāng)村生態(tài)污水處理廠,讓清澈的溪流重新歡唱;打造鄉(xiāng)村多功能綜合樓,讓朗朗書聲蓋過呼嘯山風(fēng);平整當(dāng)?shù)氐谝粋€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足球場(chǎng),讓孩子們?cè)谇驁?chǎng)肆意奔跑歡笑。
2024年7月,已經(jīng)轉(zhuǎn)戰(zhàn)東蘭縣金谷鄉(xiāng)隆明村掛點(diǎn)幫扶的周理接到了那個(gè)期待已久的電話:“周哥,我考上廣州大學(xué)人工環(huán)境工程專業(yè)博士了!”電話那頭的聲音微微發(fā)顫。周理望著眼前連綿的青山,恍惚看見7年前那個(gè)攥著錄取通知書手足無(wú)措的少年,淚水模糊了視線。他聽見覃福雨輕聲說(shuō):“周哥,我做到了。”簡(jiǎn)短的6個(gè)字,背后是7年的堅(jiān)守與蛻變。
因?yàn)樽约涸苓^雨,所以更懂得為他人撐傘。如今的覃福雨,正將這份溫暖繼續(xù)傳遞。開頭合影中那張青春洋溢的面孔——來(lái)自崇左困難家庭的周標(biāo)勝,正是這份傳承的最好見證。出于經(jīng)濟(jì)考量,周標(biāo)勝研究生畢業(yè)后,本不打算繼續(xù)深造。覃福雨鼓勵(lì)并推薦他報(bào)考自己導(dǎo)師的博士生,還幫助他申請(qǐng)學(xué)校補(bǔ)助。求學(xué)路上的少年不再踟躕,周標(biāo)勝如愿考上了廣州大學(xué)的博士,成為覃福雨的同門師弟。從受助者到助人者,覃福雨用行動(dòng)詮釋著夢(mèng)想的傳承。
在最近的通話中,覃福雨向周理吐露心聲:“畢業(yè)后我要回家鄉(xiāng)工作,像您一樣扎根基層。”他動(dòng)情地說(shuō):“當(dāng)年您為我點(diǎn)亮的那盞燈,如今我要讓它照亮更多山里孩子的前行路。”
“鄉(xiāng)村振興需要一代代接力長(zhǎng)跑,而教育振興就是這場(chǎng)接力賽的關(guān)鍵一棒。”周理感慨道。曾是貧困村的隆明村是“九分石頭一分地”,如今通過養(yǎng)六白黑豬、種桑養(yǎng)蠶、直播帶貨等,村級(jí)集體經(jīng)濟(jì)收入已突破百萬(wàn)元,嶄新的學(xué)堂里,孩子們的朗朗讀書聲也比以往更加響亮。“前幾天,奶奶給了我8000塊錢,我把它們捐給村委會(huì),作為村里孩子的讀書備用金。”在周理看來(lái),讀書是改變命運(yùn)的最好方式,他希望每個(gè)村的孩子都能擁有光明的未來(lái)。
從周理、覃福雨到周標(biāo)勝,再到更多受助學(xué)子,這場(chǎng)關(guān)于夢(mèng)想與希望的接力賽,正在八桂大地上書寫著最動(dòng)人的篇章。
本報(bào)記者 尹丹丹





